贴身照护一个老人九年,是什么样的体验?
很少有人能给出一个详实的答案。关于「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部分人所知不多。我们倾向于相信,「老」是一件能够被钱解决的事,好的医疗机构,好的养老院,但郭强生不这么认为。他已经照顾自己的父亲九年了。
2013年,郭强生的父亲确诊失智。他必须面对一个选择:是继续自己的事业,把父亲放在养老机构,还是回到老家,照顾父亲?那时,他在台湾「东华大学」任职,是创作与英美文学研究所教授。他从高中开始写作,拿过各种文学奖,是业内知名的写作者。如果选择后者,一切都要归零,他要用自己的人生来置换父亲的晚年。
两年后,他决定停薪留职三年,回到台北照顾父亲,直到今天。这漫长的九年,郭强生一直说起这个时间长度(采访于2022年底进行)。长期照护的生活是机械的、繁杂的,郭强生觉得自己离外界越来越远,他时时感到疲累,正如日本记录家庭看护者困境的《看护杀人》一书中写道:「长期压抑的家庭看护者,他们的压力就像是在空杯子上慢慢加水,快到杯缘处,似乎还能承受,等到再满上,压力就如同杯中的水满溢出来,崩塌殆尽。」
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郭强生窥见衰老的真相。老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一点一点发生的。但整个社会尚未准备好照顾老人到九十多岁甚至一百岁。社会对老年的展示,走在两个极端,要么用花花绿绿的词语包装「老」,强调老人要「乐活」,要么把老去的过程说得凄凉恐怖。真正需要被看见的,是看护人才的流失、社会福利支持不足。
郭强生今年58岁,他和父亲,现在是两个老人一起过生活。对「老」的学习应该是当下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因为即将到来的,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老人,照顾另一个老人。
以下内容由郭强生的讲述整理而成。
一、
2013年秋天的时候,父亲也85、86了,被诊断出失智。要说失智这件事情有什么节点,真的很难判断,问题就是慢慢地、不明显地出现了。
家里那时候问题挺复杂的。我在花莲教书,给父亲打电话,他的同居人说你爸爸在睡觉。她想把我和父亲隔绝开,后来她直接把父亲的手机给没收了。有一次我跑回来,家里没人,灯全暗的,我爸躺在那边,电锅里就蒸了几个豆角跟几块豆腐,我甚至在家里发现一根很长的、放在嘴巴里的胃管。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决定要正视父亲该如何照护的问题。
那时,很突然地,我得知哥哥罹患第三期的肿瘤。哥哥生病之前,我心里仍然会觉得,还是有人可以帮你分担一点。后来,哥哥去世了,恋人又向我提出了分手。那是我最糟糕的时候。
我学会一件事情,不要再给自己找可以想象、可以依赖的东西,无谓地消耗期待。自己先开始做吧。
身边的人说,你怎么可能顾得上嘛,送养老院不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不只是解决父亲没人照顾、送养老院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么几段重要关系的话,我们要如何对待它们。照护不是责任分担或是义务,而是我的心愿。我没有婚姻、子女、家庭要照顾,我的心愿就是陪着父亲,让这个家画上最后的句点,做那个把原生家庭维持到最后的人。我们这一代同志,是原生家庭最后的照顾者。
照顾父亲,第一件事是要去找看护、外劳(外籍劳工)。那时候,台湾的养老从法条到日常事务方面都有问题。本地劳工不做24小时看护,做满8个小时就下班,那剩下的16小时该怎么办?唯一能够求助的只有24小时的住家外劳,但是申请外劳要有两位医生提供的医疗证明,证明老人真的需要。防外劳跟防贼一样,又防我们滥用医疗资源,医生也不敢随便开。
刚刚开始申请,外劳不可能那么快到,我只有一个人。问社区有什么资源,他们说中间会提供短期的社会照顾,一个礼拜免费3个小时。我问那个有什么用,他们说像托儿所那样,白天把他送去,下班就可以把他接回家,可以帮他洗澡,还可以继续共享天伦之乐。我说你听不懂吗,我家里没有别人,我人在花莲,谁早上把他送去,谁晚上把他接回来?我真的焦头烂额,三个月瘦了七公斤,实在是千头万绪。
我还要受到旁边邻居的骚扰。当时政府鼓励居民检举非法外劳,只要谁家有东南亚的义工出现,左邻右舍就可能打电话去检举,检举错了没刑责,检举到一个可以拿5000块(新台币)的奖励。
规则的制定者好像设计了一套很利民的制度,可是每个家都长得不一样。我发现,很多人没有真的想过,现代社会的家庭是怎么样的情况,每个人都用自己很有限的认知,用自己家的样子,来概括这个社会中其他的家庭。
这样子还是不能够好好照顾父亲,所以没有办法,2015年,我向学校申请留职停薪三年,回到台北。

二、
我回台北照顾父亲,大家说,你多可惜,你看你升上正教授了,在学校里头可以做个什么院长了,你就应该把父亲送养老院,你自己的人生还是很重要啊。
但我后来体会到,有什么样的机会,也是幻觉想象。我那时候也快50岁了,我到底还要什么,多做十场演讲吗?去拿一两百万的研究计划吗?我现在放弃的事情,并非全部归零,也许以后能拿回来一部分。但是父亲的家就是走向归零,全部没有了。最难的不是放弃工作,而是我要怎么做,让这个家还能够维持住。
我给自己设下了一个目标。只要父亲还认得我,叫得出我名字,我都不会放弃他。
等新的外劳进来的三个月里,照护父亲的只有我一个人。我真实地感受到看护工作就是一个机械性的劳动。从早上父亲睁开眼睛开始,梳洗、吃药、量血压、吃早点,散步,去医院回来,又要吃中饭,吃完中饭又来一遍,量血压、吃药、睡午觉,清洁家里,然后给他换衣服、洗澡、帮他上厕所,搞到11点就寝,一天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时,我会下楼去超商买杯热咖啡,坐在门口抽根烟。除此之外,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更好的奖励给自己。外面的世界都有点陌生了。我感觉自己像是来到某个远方的城市,语言不通,我无法跟任何人互动。
我发现人其实也是可以这样过下去的。50岁了,我此刻、眼下就是这种生活,虽然很单调,很茫然,但是,什么东西只是我自己想象的,什么东西是我还想要去贪图累积的,在照护的那三年,这些东西从我生命里头慢慢地退掉了。
父亲就寝之后,外劳剩下的时间就跟家人视讯。可是我没有其他的家人,把父亲送上床,就会很空,很茫然。我必须接受此刻此时就是我唯一的生活,不要去想还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在等着我,不要想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如果只是把照护当作额外的一件事情,认为我的生活不是这样,怎么多出一件事情,那会过得很痛苦。要很诚实地问自己,如果有一点不甘就不要做。
只有两种选择。你是希望跟你年老的父母再次建立一个新的、好的关系,还是想尽办法不让照护这件事情改变自己的人生?你有办法的话,就赚多点钱,把他送最好的养老院,自己心安理得,别人也没办法说话。吊在中间,两头不着,最难过。有人作为照顾者,会崩溃,但那个崩溃不是来自劳务本身,是自己的生命状态也有了问题。
我和那些结婚、组建家庭的同龄人,最大的不同是时间的调配。如果我组家庭的话,好歹我去照顾父亲的时候,可以说,老婆,你去帮我跑一下银行好不好。或者叫小孩,你去给爷爷送个东西。但是现在只能由我一个人做。时间总是不够用,有一阵我的口腔里长了个息肉,发现后一直没时间去做化验割除。
只能学会对其他事情say no,很多的演讲、邀稿,我就说no,很多找我去做评审,我就说no嘛,我要留出空的时间来,以应不时之需。
照护以后,我十年没有离开过台湾,即使在台湾本地,顶多去当天能赶回来的地方。老人家小事情多,前一阵子,夏天的夜里,父亲突然开始发烧,会哭闹。我心想糟了,如果吃了退烧药,到三四点还不退烧的话,可能就要送医院了。我一整夜都不敢睡觉。直到今天,我还是得一直在他旁边,不可能让人暂时接手一天。离开远了,事态可能就会急转直下。
照顾一个衰老的人,不是突然发生、很快就会结束,这是长期抗战,得先有这样子的认知。
三、
这些年,我一点点看到,人老的过程当中,到底会遇到什么。
父亲不是从不能自理那天开始就成了化石了,不是这样的。不能自理,是功能上发生的事情。你让他很快组织比较长的句子,来描述他自己的想法,这件事他会吃力,会有一些奇怪的表达方式。
不管冬天还是夏天,我父亲总是会问我,你冷不冷?他不是分辨不了季节,他只是想要问问你,你好不好。原来那种表达的路径走不通,他绕了另一条路。我觉得大家一直有个错误的观念,要把老人训练成正常的样子。比如说,老人的手在身上摸,你说不要摸、不要弄,你在干吗啊,停下来。其实他出现的新状况都是新的表达方式,表达他的不舒服。
一位朋友说,他父亲的性格改变了。我回答他,你怎么知道以前你以为的他的性格是正常的?也许现在那个贪吃、暴躁、疑心病重的老人才是真正的他?有没有可能他们这些行为始终在进行,只是一直没被我们发现。家庭也是一个规范系统。我们只记得父母总是在要求我们修正自己,但是绝大多数的父母被婚姻、子女修正的程度,也许他们自己到后来都无感了。等到人老了,对于社会规范与监视加之于身的警觉退化,也不懂得隐藏了,可能真正的自我才显现出来。
成为一个被照护者,父亲最开始是不适应的。他完全不是教科书上的老人,那种要把他当作幼儿般照料的说法,根本不成立。请第一个外劳的时候,他们冲突很大,一有什么不如意,我父亲会动手。只要我跟外劳讲话的时间一长,他就很想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露出急躁的表情。
有段时间,他突然不吃东西了,一下子瘦了十几公斤。我想送父亲去医院,医护朋友说,送来我们也只能插鼻胃管,做不了什么,那个也很不舒服,就是灌食。我开始在家里观察和研究父亲。观察了两个多礼拜,我发现,他吃饭的时候,外劳会先装一碗稀饭,把菜统统铺在稀饭上面,拿汤匙舀了给他,他根本就不张嘴。
我猜测,他不吃饭可能有其他原因,跟他的眼睛有关系。他不太能够拿筷子,也看不清他要夹什么东西,但不想要外人知道。我们弄一碗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他张口就吃,让他感到自己像废物一样,所以他不吃了。后来,我跟外劳说,你还是每次做出来三道菜,摆在盘子里,用筷子夹给他,问,爷爷,要不要吃鱼?爷爷,要不要吃蛋?这样,他还是在这个家里头,跟大家一样在桌上吃饭。慢慢地,他就开口吃了。
那是我刚开始照顾他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不知道是自己照顾,还是把他送养老院。他也怀疑,大儿子死了,同居人也跑了,这个小儿子可能过几天就把我送走吧?庞大的未知会成为恐惧,恐惧就让人焦虑失常。我想,父亲那时候很暴躁,很不安,也是因为我没有下定决心。过了一个多月,他慢慢发现,没有人要把他送走,儿子一天到晚在身边,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对照护来讲,陪伴可能比医疗更重要。
父亲一餐饭要吃上两个钟头,大半时间闭目打坐,想到才挑一筷子。我渐渐抓到了诀窍,照顾老人就是要一个「慢」字。有话慢慢说,说快了他就不理你;散步慢慢走,走快了他就要回家。吃饭当然也得慢慢来。当我把整个周日都设定为空档,一种不需要做任何事的状态,我与他的频率就慢慢开始接近了。后来我的生活也因此多了许多无所事事的周日。
你不要以为老人有点迟缓,就感受不到你的情绪。他们只是外面的硬体磨损了,核心感受他会知道。你如果抱着不甘或者冷漠,还有很多的情绪,自己没有办法平复的话,被照顾者感受得到那种气氛和压力。
有时候在外面吃饭,我看到旁边一大桌三代同堂,有爸爸妈妈和小孩,旁边有个外劳陪着一位坐轮椅的老人家。那天,那位阿公在庆生,但是其他家庭成员就是在聊他们的事情,儿子你在国外念书怎么样,爸爸妈妈你们接下来旅行怎么样,虽然把阿公也推出来了,可是从头到尾只有外劳在喂他吃饭。很显然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人想要跟阿公互动,他根本不在这个家里头。
所有担任照护的人都要知道,失智是不可逆的,顶多就是不要让他继续恶化,不可能变得跟以前一样。你不能说你要训练他,好像鼓励老年人多爬山,体力就会变好,不是这样。最好的方法就是花时间注意他的详细变化。
父亲是画家,刚照护他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字、画、书法,都没有兴趣了。这个过程我试了很多方式去诱导,让他对一些事情恢复兴趣。看他写书法,我就可以大概判断他的精神、体力怎么样。2018年到2021年,这三年,他又开始写字、画画了,可以写中楷,精神集中,腕力很好,后来只能写大字了。那段时间想起来就很珍贵。他写书法写了好几大本。跟他这些互动当中,我想到,我也50几岁了,我们现在是两个老人一起过生活。
我今天看到的父亲就是自己未来的样子,我在照顾他,也在学习以后怎么照顾自己。

四、
听说我换看护的过程,一个出版界的前辈和我说,搞不好你比你爸先死咧,这就是给你这种不结婚的人的惩罚。她幸灾乐祸。还有人说,哎呀,你真倒霉。我听了这话很震惊,她也终生未婚,也经历过父亲长期卧病,怎么会把家有老人需要照护这件事,用这么偏激的语言丑化?我怀疑她打心底厌恶照顾自己卧床父亲的那段记忆。
整个社会告诉我们,育婴是幸福,去做老人的照护者就是不幸,所以等到要面对它的时候,大家会这么慌乱。在台湾,你请育婴假,留职停薪的话,只要填了单子,一定可以申请到,两夫妻轮流各请三年,而且不得拒绝申请。我为了照顾父亲留职停薪,叫做「侍亲假」,要一年一请,一年一年地续,还要经过学校各级单位核准,系上要帮你配合。
大家觉得反正老人就是风烛残年,你请个一两天假赶回去,送了终,最后一面见到就好了。你父亲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需要一年两年吗?错了,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这样。老人卧病的时间十年、二十年是常态。照顾老人,我已经进入了第十年。
所以大家要有共识,这是我们的生命生活,而不是认为怎么这个问题落在我身上。这关乎整个社会的配合。过去,阿公、阿嬷们一起过,他们送走了自己的祖父祖母,再送父亲、母亲,这个仪式生生不息,环环相扣,本来就是社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但战后五十年,我们学美国模式,医疗、养老走向系统化,把它从家庭生活分出去之后,大家对「老」这件事情才变得越来越陌生,才有了恐惧。现在我们发现那个体系没有准备好照顾老人到九十多岁,甚至一百岁。原来的设计不行了,那该怎么办?把老人接回来,大家又不愿意,又很怀疑。
我们对衰老的恐惧多多少少被煽动起来了,「独居老人」、「孤独死」,死了之后几个月才被发现什么的,社会的话语字里行间把衰老讲成一个恐怖的事情。
有一天我跟朱天文聊天,为什么广告商一天到晚拍老人就要去爬山、老人要动,要动你才活得久?我非常不能理解。一天到晚谈的都只是肉体机能的事情,大家都以身体活得久为目标,我们觉得这个目标很奇怪。科学也好,商业也好,好像一直在促进大家的共同目标跟共识,但这件事情不需要什么共识。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你自己最了解。
还有人说,年纪大了,要多跟年轻人接触,自己才不会老化,要学习年轻人的言语。我后来想,什么事情真的让我心里有感觉到年轻呢?是当我听老歌的时候,那种青春的感觉。你年轻过、青春过的感受,是你自己的,你跟年轻人混在一起的「年轻」,是你包装出来的,内心并没有那样的悸动,没有活水源头。你不回忆,不回味,不拒绝,只有外面的一个壳,你已经跟二三十岁完全切断了。我们年轻的模式是一直在的,不必再去装出另外一种「乐活」。
我比被照护者的父亲那代幸运一点,他们没有料到自己会活这么久,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这一代,这件事情我是真正认知到了。做出最后决定那天还没有到来,但是我在这个准备过程中累积经验。我相信,我不是在慌乱的情况之下做了什么决定。
我从小喜欢阅读,一直觉得跟周遭的同龄人有一点距离。青春期之后,我发现自己是同志,开始知道这个世界是为异性恋准备的,不是为我准备的。这个过程充满了挫折、忧伤。我从来没有觉得被社会、世界接受过,又何谈老了以后被他们遗弃呢。在照顾父亲的这十年,更加体认到孤独是很正常的状态。我不知道以后的下一代,下下一代,片刻都离不开手机、完全无法独处的这一代以后怎么办。那也是不一样的课题。以后他们要照顾的父母可不是这样子长大,不是这样子看人生的。他们要真正了解父母是谁,是怎么活过来的,才能做到真正的陪伴。
五、
朋友们谈起养老,大概分成三派。一派就是,到时候再说吧,一派很担心,焦虑,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还有一派拼命在买长照保险、养老保险,他们说,老了就住养老院,不要麻烦子女。
除非以后有重大改革,现在台湾所谓的养老院只有两种。一种是收卧床老人,叫安养中心,进去就是等死。另一种叫做养生村,只收还能够自理的老人,给他们安排了瑜伽课、画画课,还能唱卡拉OK。但养生村又是一个小型社会,里头也会有排挤,有嫉妒,有八卦,搞不好还有霸凌。住进去一定要常常有人去看你,如果跟我一样单身,顶好不要住养生村。知道你没有人来,照护人员是会大小眼的,来的那个人还要送红包,说请多多照顾。
我分析了一下,我从小就是不喜欢团体生活的人,可能半夜12点钟才跑去买东西吃。住在养老院会饿死,养老院多半开在山明水秀……也就是荒山野地里头。完全跟着大家作息,我会很痛苦。我不能接受的是,住进养生村最多就是个小单人房,我所有的书、收集的DVD,统统就要丢掉。对我而言,这些东西不可能跟我切断的。很多人觉得,住进养生村里头,好像拿到了移民的绿卡一样,可那是我真正的生命状态吗?跟我这个人真正的生活需求,是不是相符呢?
我最后会选择居家养老,但绝对不能请护工。外劳不是机器,偷懒真是难免。父亲还有我在看着、管着外劳,到我,就没有了。所以我现在能做多少,能照顾自己多少,就先做了,看外面的环境怎么变化之后再调整。对于老这件事,自己要先接受,我不能逃避。大家先认识老的过程是什么,你才能为自己做出最适合的选择,再朝自己的目标努力。我现在慢慢地让自己的生活作息正常一些,以免有一天我真的非得住进养老院。
很多人觉得,养老照护是医疗体系要想的事情,好的养老就是有好的医疗设备,好的养生村,其实不是。大规模的科技、医疗、社会、法律要一起动起来,看看有没有新模式会产生。我看到的新模式里头,养老社区化比较符合目前的真相,北欧国家现在在尝试把一些小社区维持恢复到1970年代、1980年代的样貌,让整个社区参与进来,让老人按三四十年前的方式活,电话还是转盘的,领钱还是用提款卡,买东西还是杂货店。让他们用这一套方式活,他们衰老的进程会延缓。
像我父亲情况稳定的背景是,我让他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熟悉。他住的地方没有更动东西。他的字、画在哪里,洗手间在哪里,是他下意识的直觉反应。老人会觉得老,不是智能出现问题。对他来讲,学一套新的东西才是加速衰老。我们现在的环境一直在改变,人还没老就先变得封闭了,反而是加速老化。
六、
前两年父亲写字、画画,我帮他磨墨、备纸,找字帖,都是些小仪式。他的牙口越来越差,肉嚼不太动,一直得换食物。最近我教外劳把嫩豆腐、萝卜做成卤味,那时我想到,这是小时候看爸妈做菜才有的记忆,因为有这个家,我才知道这些事情,菜怎么准备,父亲写字、画画怎么准备。
但别的东西没话讲了。我和父亲之间,只是靠着一些旧的事情在联系着。
母亲死了以后,丧偶的父亲好像觉得得到了某种自由,想要发展他要的老后生活。那时,我每周末从花莲赶回来,陪父亲几天再回学校。但父亲却对我不耐烦,有一天开口要我搬出去。
后来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和父亲两个人都在展开各自的人生,是疏离的。反而在照顾之后,我和他的关系又回到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每次问他,我几岁?他说20,我说那你几岁呢?他说他40,都乱说了(笑)。很奇怪,他知道我在教书,今天有没有课、你冷不冷,这是他最常问的两句话。
我和他有剑拔弩张的时候。他怨我不结婚,我和他半开玩笑,说我要是结了婚,就要忙着管我自己的家和小孩,就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照顾你。他脸色骤变,说我要你照顾?你照顾得了我什么?我有退休金,满街的人我还怕找不到人来照顾我?你滚远一点!我只感到极度的疲倦,用最冷静、最不带情绪的语调,打断他,和他说,不要再跟我闹别扭了,以后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和父亲早早不合,一辈子不好。大学一毕业,她就嫁到比利时去,想离开那个家。近几年,她看了我的《何不认真来悲伤》,跟我讲,她以前一直觉得她父亲要向她道歉,现在终于决定放下了这个心结。她父亲90来岁,还得了癌症,最后这一两年,疫情期间,她一趟一趟地两边跑,2022年暑假给父亲好好地送了终。她说,我爸到死都把我当死人,只爱我妹妹,可是无所谓了,这就是我爸爸。和解是她单方面完成的,她觉得那是需要做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直到独力照顾老去父母的时候,才会了解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才会原谅曾经父母对我们的照顾如果有任何疏忽和失手,是多么不得已。身为照护者才会了解,我们自己也一直在犯错,也一直在学习。
母亲走的时候我才37岁,还不太懂真正陪伴的意思,家人真正能够提供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失恋翻来覆去地说得事无巨细,但对于从家人那里得不到的、遭背叛的或被误解的情感,总是陷入失语的境地。
直到照护父亲,我在里头我真的学到了、认识了,我是从这个家里来,所以我就成了我这样子的人,体会到这种相连的感觉。是我需要父亲,我赖在父亲身上,怕离得太远,就会失去自己跟家这件事的最后联结。
我最想要探索的,是一家人感情纠结的缘起,和后来挥之不去的疏离。我只知道,生命中其他消失的过往,我都可以放手,但这次不能。我只有一个家,不想等到一切都过去了才来哀悼、怀念。
2018年,我和父亲渐渐建立了比较规律的生活。他的看护和医疗,一个月的基本开销是6万(新台币),除了他的退休金,我每个月都要贴钱。我需要一份工作,需要重新厚着脸皮出来跟年轻人竞争。那年我转任到台北教育大学,这个系主打的是语文与创作,现在就全力在教学。我上课教教学生,下了课照顾父亲,或者写作,有空就翻出自己喜欢的老电影,上网去听老歌。
三个月前,父亲开始全天穿纸尿裤了。我还没给他打疫苗,他96、97岁,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很小心,在家里都戴着口罩。当下就是要平安度过这一关。现在他不会每天都有状况,隔一阵子,天气变化了,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马上就要过年了,这十年来,每年的年夜饭我都是好好准备的,每一次朋友都说,家里就你跟你爸,忙活什么呢。我说这一定要的,就算我爸不在了,以后我一个人过年,也要忙活,我要买花,我要准备年菜,准备春联,这些事情我都要做。很高兴,又是一年了。
文章来源: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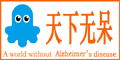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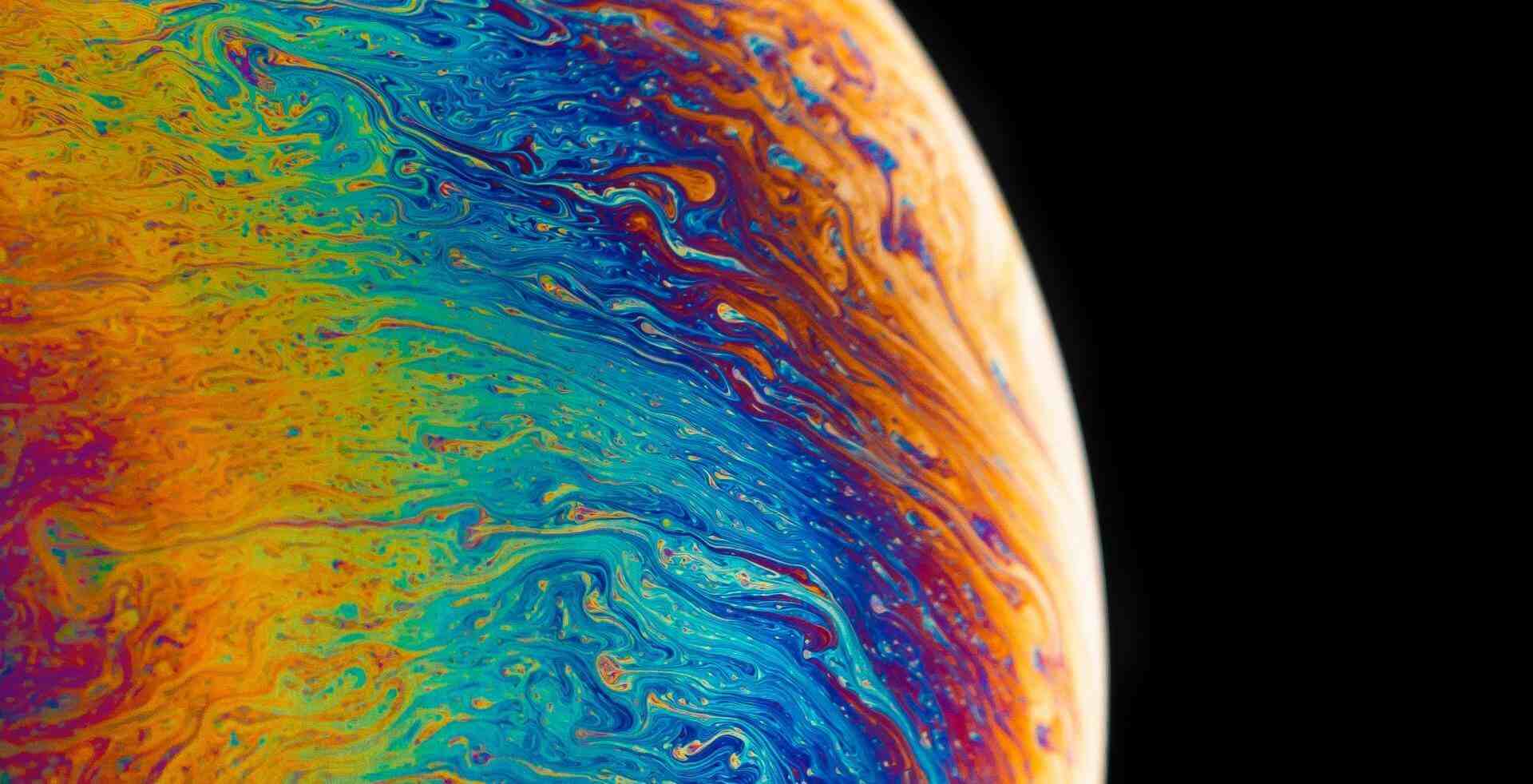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