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后,我默默地希望这一切就是一个大错误。
随着阿尔茨海默病缓慢的进展,还有时间怀疑。也许诊断是错误的,记忆的空洞和找不到合适的单词或许只是正常的老化。在你的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丝希望。
但总有一天,否认不再是一种选择。就像阿尔茨海默病本身一样,这一刻慢慢到来,注意不要太快地放弃。最近,当我路过宾夕法尼亚州新希望市中心的雄鹿县剧场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的丈夫蒂姆和我最近在那里看了一场演出,我甚至记得和谁一起去的。但我不记得我看到了什么节目。蒂姆提醒我这是“男人和玩偶”(Guys and Dolls),但我的记忆并不存在。没有歌曲,没有故事,没有场景。什么也没有。第二天早上,我静静地坐在床上。 “蒂姆,”我说,“它来了,不是吗?”蒂姆没有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轻轻地说,“是的,它来了。” 我哭了。显然,我已经知道改变即将到来。作为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我接受了两年多的测试、刺激、注射和研究。但回首过去,怀疑的阴霾一直笼罩着我。
阴霾消失了。希望的火花已经熄灭了。现在我们必须认真规划未来。阿尔茨海默病将继续从我脑中偷走记忆,除非出现不太可能的医学奇迹,否则没有什么能阻止它:记忆力的丧失,活动能力的丧失,自由的丧失。尽管如此,我并没有认输。在内心深处,我知道生命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还有时间去战斗和爱。
确诊以后并非所有的一切都很糟糕。在得知自己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几个月后,我和相处12年的伴侣登记结婚了。我姐姐、侄女和侄子跟我们一起拍了照片,我们第一次以夫妻的名义接吻并履行了犹太人打破杯子以求好运的传统。
我还被邀请参加阿尔茨海默病协会的全国咨询委员会。在长达一年的任职期间,我学到了很多很棒的宣传知识和研究,并在全国各地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讲。我遇到了最令人惊奇的一群人,包括那些痴呆症患者和那些每天努力工作以阻止疾病的人。
我也很幸运能够继续工作。我工作的那个小小的非营利组织允许我辞去董事的职务,继续兼职担任领导职务。我无法想象没有工作和目标的生活。
我也坚持了已经持续了八年的锻炼。从CrossFit(为混合健身,也称全面强健,最近几年国外流行的一种训练方式,包括体能,力量,爆发力,速度,协调性,柔韧性等)到骑自行车,以及所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运动,我每天都做些运动来促进我的血液循环。虽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没什么意思,但我确实喜欢。我相信研究表明,它有助于延缓阿尔茨海默病进展。
说到研究,我一直在参加一种实验药物Biogen's aducanumab的临床试验。在16个月的“双盲”阶段,我接受安慰剂或实际药物。现在我正在参加一个开放的阶段,我保证会收到测试药物。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对这种疗法产生过负面的反应,并且我见过许多努力寻找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方法的好人。
我经历过的最明显的阿尔茨海默病症状是持续不断的寻找合适的单词。我会在聊天时,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我感觉自己好像跌入了空虚之中,通常只能用简单的手语来表达自己。有时候,在挣扎了30秒钟后,这个词就会出现在我脑海中。其他时候,它就是不见了,不管我和谁聊天,别人都会玩的一个我想说什么的猜谜游戏,而这会让我沮丧得流泪。
事实上,流眼泪似乎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一天晚上,我和家人坐在一家餐馆里,发现自己累了,突然开始哭起来。我停不下来,尴尬地挥手,蒂姆和我最后离开了餐馆。直到30分钟后我们回到家里,我才停止了哭泣。这是漫长的一天,但眼泪却毫无意义。还有一次,在紧张的会议后,我可以感觉到我的情绪很低落。办公室一空,我就抽泣起来。有趣的是,我从来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但现在因为焦虑而吃药,这可能是我现在爱哭的原因。
阿尔茨海默病也归咎于孤独感的增加,当我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孤独感会导致自杀。面对失去理智的现实是毁灭性的。再加上害怕无助,什么事都依赖别人,有时候,结束一切似乎是明智的选择。我同意那些热切地认为辅助自杀或所谓的理性自杀是一种人权的观点。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我还有很长的生命可活。我会继续下去,爱我的家人和宠物,尽我所能努力为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而工作。我将继续进行药物试验——不是为我,而是因为我想让这种疾病消失,以便后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侄女、侄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不必面对阿尔茨海默氏病,也不必看着他们爱的人逐渐消失。同时,我向那些以我的名义向阿尔茨海默病协会表示支持或贡献的人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支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但我也提醒他们,如果我忘记了,请不要惊讶。请不要生气,如果你需要重新介绍自己,并提醒我关于共享的记忆。
我还要再战斗一段时间。但对未来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Philip Gutis是《纽约时报》的前记者,她在2016年被诊断为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
By Philip S. Gutis
编译:袁波
文章来源于 阿尔茨海默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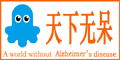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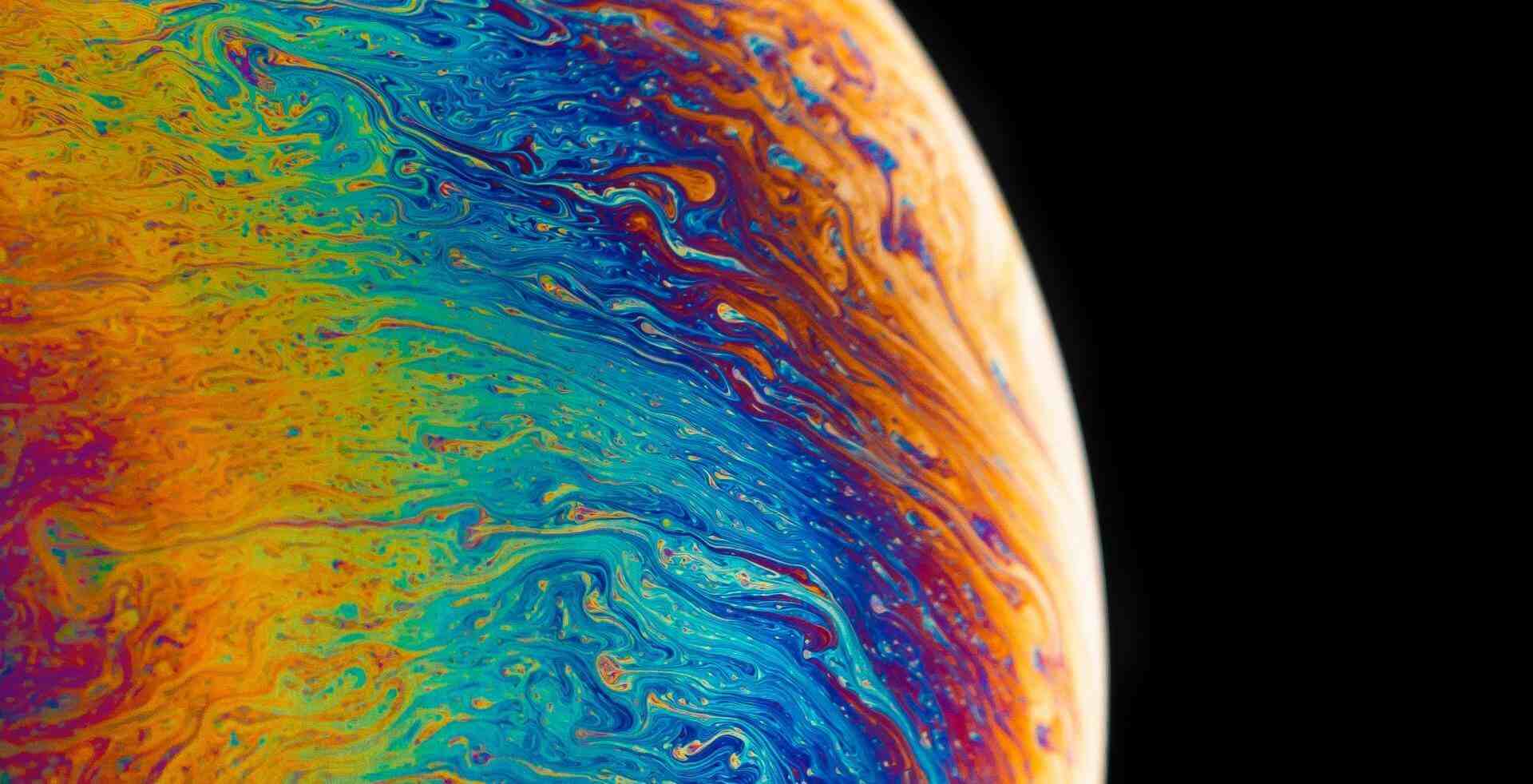


评论 (0)